自2013年逐渐隐退后,大家都以为刀郎真的“封刀”了;没想到他却寂寞地磨刀十载,携带着新专辑《山歌寥哉》强势回归。

这张专辑中的《罗刹海市》更是成了大众瞩目的焦点,其所掀起的热潮不能说绝后,但在互联网的加持下能算得上空前了。
短视频平台的各类博主纷纷学唱、翻唱,笔者甚至刷到了一条豫剧翻唱。
关于这首歌的讨论,自刚一推出就立刻冲破了音乐圈以及音乐本身,启发了大众对音乐圈乱象、甚至是更广泛的社会现象的思考。
与刀郎以往粗犷、豪放的民歌曲风不同的是,这首《罗刹海市》在保留了刀郎一贯的民歌风格的同时,还融入了摇滚、电子、说唱等多种元素,曲调复古婉转,歌词更是诙谐幽默,讽刺拉满,让听者自觉地去对号入座,例如:
“她两耳傍肩三孔鼻,未曾开言先转腚”,这句词让人们立刻有了画面感:台上唱歌的刚开嗓、导师的座椅就转了过来,大喊一声“I want you”;
“勾栏从来扮高雅,自古公公好威名”,回应了高公公当年吹捧旧社会勾栏青楼的那句“勾栏过去都是高雅的地方”;
……
要说这首歌没有嘲讽那几位把持歌坛话语权的大哥大姐,恐怕是没几个人会信的;但如果把这首歌仅仅看作是刀郎“磨刀十载的复仇之作”,那就太小看刀郎了。
通过对刀郎过往人生经历的观察,笔者相信刀郎是懂哲学、懂辩证法的。娱乐圈(juan)说到底,也只是社会这个庞然大物的冰山一角;娱乐圈曾经发生的一幕,每时每刻不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普遍地发生着。这首歌表面看来是刀郎对自身曾经遭遇的不公经历的愤懑,实则是替受压迫的草根阶层喊出了对士族门阀的愤怒。
《罗刹海市》是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中的一篇,讲的是商人之子马骥的一场“奇幻漂流记”,写了罗刹国和海市(龙宫)两个世界:罗刹国是一个虚构的国家,那里的人以丑为美,越丑越是担任高官、掌管朝政,完全是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,蒲松龄借罗刹国揭露与讽刺当时的社会现实,表达心中的愤懑与不平;而海市恰恰与之相反,这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,环境美、人物美,重要的是政治清明,寄托了作者的社会理想。然而,蒲松龄最后也感慨,这种理想只能“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”。

看了蒲松龄的原著,你还会以为刀郎只是在“夹带私货”、“挟私报复”?刀郎在新专辑《山歌寥哉》的推介语写道:
《山歌寥哉》是继《弹词话本》后,结合了聊斋文本与民间曲牌印象的主题概念专辑,此系列尝试构建流行音乐与民间传统文化共生共存的音乐生态。明代新兴市民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全新审美意识的开始《聊斋》继承了冯梦龙对于市民伦理的认同观念,描绘了现实之境与理想世界、男与女、善与恶、债与偿、强与弱、神圣与亵渎,充满了对立虽然现实与幻境都伴随着各种残缺,但《聊斋》绝不是幻灭的悲歌,其中的许多篇章都充满了理想的光辉,是我们得以管窥那个不属于我们的时代之洞眼。然以我观物,故物皆著我之色彩,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图样,本专辑的+一首作品则是属于这个时代的“山歌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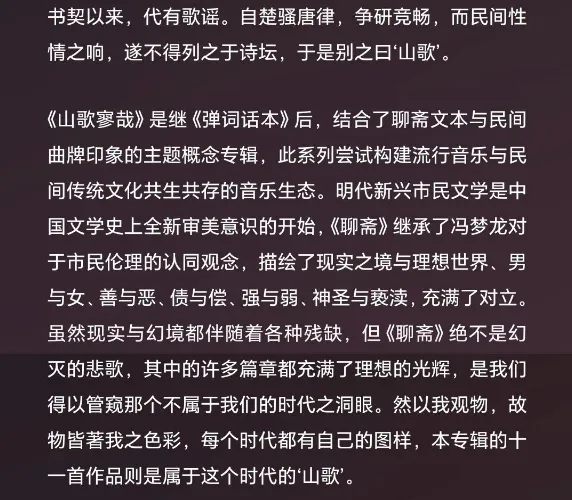
《山歌寥哉》的序曲,歌词极简、却唱出了刀郎的“野心”:
九州山歌何寥哉,一呼九野声慷慨;
犹记世人多悲苦,清早出门暮不归。
摊开《山歌寥哉》的专辑,致敬的正是蒲松龄的“功业无成百事哀,愤而泼墨著聊斋。描狐绘鬼倡情义,讽世讥时申旨怀。”

《罗刹海市》、《颠倒歌》等曲是对不公现实的直讽;《花妖》、《镜听》等曲虽也是“情歌”,却由妖鬼真情义反衬现实社会的人性凉薄;《画壁》、《翩翩》、《画皮》等曲唱的是世间的虚妄与迷惑;《路南柯》、《珠儿》、《未来的底片》等曲则是寄托了刀郎的理想。
这样的刀郎,早已超脱了个人私怨。
然而,这个专辑能否撑起刀郎的“野心”,笔者却是持怀疑态度的,除了《罗刹海市》因为其所引起的争议话题被广泛传播,其他歌曲如果没有一点文学功底,恐怕真不好理解,要引起广泛传播恐怕并不容易。

不过,对于刀郎的努力,笔者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:
在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,刀郎能够超脱个体去努力思考社会问题,通过致敬经典来叩问现实,最终呈现出来的思想性水平究竟如何,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,但这种态度无疑是可贵的;
在一个急功近利、抄袭成风的音乐圈,刀郎自打出道以前就一直坚持做民间采风,保持曲风的地方性,力图复兴民乐,试问今天还有几人能够坚持、能够做到?
出生于四川省资中县的刀郎,2004年之前在新疆生活居住了10年,在物欲横流的大时代,他只身深入到新疆广袤的沙漠戈壁去寻找生命的曙光,去探寻音乐的灵气,深入南疆各族群众家中去体验生活的疾苦,去艰苦地方体验生活的艰难和抗争;2005年开始,刀郎更是将自己的采风放到了全国很多地方,经常就是带上几个本子和一把琴还有一些录音设备,独自出去采风……

2008年刀郎陪同臧天朔、凤凰传奇组合到新疆采风
如此才促成了刀郎的音乐风格——大众的、人民的、朴实的——也正是掌握话语权的音乐“精英”们所讥讽的“土味儿”。所以,刀郎的歌是“俗”,但却是“大俗”而非“小俗”。对于那些看不起刀郎的人,笔者想引用周总理的一句话评价:“人民喜闻乐见,你不喜欢,你算老几?”
而沉寂了十年的刀郎,仍旧在坚持这个风格,新专辑便是融入了靠山调、红柳子曲牌,以及西河大鼓等民族传统音乐曲风,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去创作,从而完成了从“大俗”到“大俗大雅”的升华。
回到本文的标题,笔者所希冀的“人民文艺复兴”,一方面是音乐创作从艺术角度向人民性的回归。
回首新中国历史,民间采风、弘扬经典是毛泽东时代音乐工作者普遍采取的做法,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、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等一系列闻名全球的传世之作,以及一系列歌颂革命、歌颂人民的经典红歌,几乎无一不是从民间、从传统经典中获取灵感的,那时的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的是“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”创作方向。例如,为了创作《黄河》协奏曲,殷承宗所在的创作小组,深入黄河沿岸体验工农兵的生活,历时近一年才完成了作品。
上世纪80年代以降,港台音乐率先涌入,抄袭西方、抄袭日韩的风气也随着涌入,例如人们调侃的“中岛美雪一个人撑起了华语歌坛的半壁江山”,再很少有人去勤勤恳恳、扎扎实实地去搞民间采风。由此可以反衬出,这么多年来始终坚持民间采风的刀郎等人,是多么得不容易。
“人民文艺复兴”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从思想角度向人民的回归,简而言之就要为人民歌唱。刀郎以前的作品虽然也有很多情歌,俗却不低俗,从歌曲中我们可以听到植根于壮丽山河的粗犷,可以听到对底层劳动者的饱含深情。而新专辑中,我们更是听到了刀郎对精英阶层以及丑恶现象的鞭笞。
一场人民文艺复兴,当然远远无法靠刀郎一个人去进行,只是因为刀郎新歌所引发的如此广泛的讨论,才让笔者产生了如此不切实际的幻想。
事实上,这么多年来,也并不是刀郎一个人在坚持:如《谁杀死了那个石家庄人?》一文中提到的,以下岗工人作为创作背景的摇滚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的《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》、说唱歌手GAI的《威远故事》等;又如前些年活跃在北京、长三角、珠三角,为流水线工人歌唱的几家打工者乐队,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北京的新工人艺术团;新工人艺术团如今更名为了谷仓乐队,他们又开始了“村歌”计划,深入到偏远山区的农村进行采风创作,与农民座谈……

谷仓乐队重庆忠县竹山村采风
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人民文艺复兴的努力与尝试。
而真正的人民文艺复兴,需要有更多刀郎式的人物的加入。笔者相信,现实会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加入,文艺界自身的内卷也会倒逼越来越多的人加入。
到那时,遥不可及的“幻想”才能变成触手可及的“理想”。








